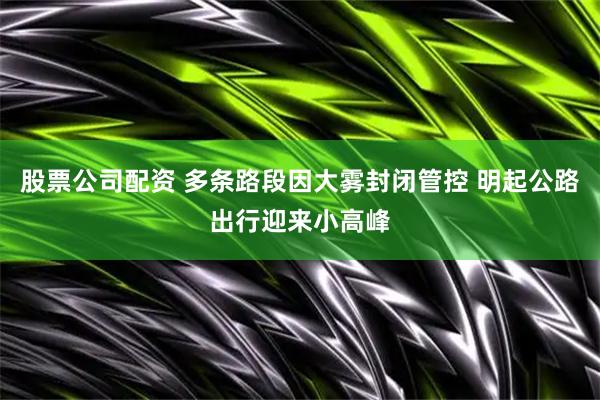作者:小季新股配资服务官网

在《红楼梦》的一百二十回本面前,很多代读者通常不会想得太多:书既然完整,自然出自一人。
然而,真正的红学研究并不是从“接受”开始,而是从“怀疑”开始。
我们现在都知道,是胡适最早提出“后四十回为续作”,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过他是怎么推出来的。
胡适最早的怀疑,是出于对程伟元的不信任。
程本序言,称后四十回是多年从藏书家及鼓担(货郎担)偶然购得残稿拼接而成;胡适觉得“世间岂有如此巧事?”认为此说是为掩盖高鹗续作而虚构的托词。
他于是开始追查。
最早发现的是一个很小的记录:清代诗人张问陶《赠高兰墅同年》诗注:“传奇《红楼梦》八十回以后,俱兰墅所补。”。
高兰墅就是高鹗。诗名题赠“同年”,自然是同科,这是很铁的关系,按说是绝不至于出错的,但兹事体大,胡适还是去查了,确认两人系乾隆五十三年同科举人,属直接社交圈。
那这个事实应该是靠谱了。
但争议还是有的,就是对这个“补”字的定义。
胡适倾向于“续作”,而也有不少人觉得是“修补”
于是,他又找到袁枚的记载。
在《随园诗话·补遗》中,袁枚写道:“(曹寅)其子雪芹撰《红楼梦》一书,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”
此话其实也算不上铁证,因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还是儿子,在这里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指向。
但有一个重要价值:袁枚并未说“写完”,他只是说“撰”。这是清代文士对“未竣之稿”的常用说法。
把这句话与张问陶的那句“八十回以后俱所补”放在一起,就形成了证据链——有人承认曹雪芹写此书,有人承认后八十回之后有人补写,而两人都在清代生活,时间上也接近。
更关键的材料来自于敦诚与敦敏。
这两位宗室文人曾与曹雪芹有交往。敦诚有诗赠曹雪芹:“共话中州旧家事,真成泪点湿罗巾。”敦敏亦有句:“儿时旧雨今如梦,文字飘零似断蓬。”
胡适与俞平伯都引用过这些诗,因为诗中出现的“泪”“旧雨”“飘零”等关键词,意味着曹雪芹在晚年虽然生活困顿,仍与文友谈论往事。这意味着他生命后期仍在写作,但没有留下“完稿”的迹象。如果他已经写到大团圆,不会在同辈文人之间传出如此清冷的感叹。
胡适的方式是“搜集旁证”,俞平伯的方式则更直接——进入文本本身。

他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当成两个文稿,逐条对比人物行为轨迹。
比如宝玉:在前八十回,“功名”一词在他嘴里等于侮辱,而在八十二回以后,他变得“勤看书,日以课文”,甚至在八十五回中“梦中见父,心折而悟”。
俞平伯认为,这不是人物成长,而是人物换了一个写作者。
另一个关键对比,是脂砚斋批语的伏线失效。
脂批在前八十回中反复提到“宝玉一生当有一番大劫”“悬崖撒手处,自见分晓”——这类批语像是提示未来将有彻底的断裂。但到了后四十回,宝玉“出家”竟是披着大红猩猩毡斗篷,在一片锣鼓声中离开贾府,俞平伯称之为“富贵和尚”。一个“劫”,被续作者写成“仪式”。
俞平伯并没有立刻喊“伪作”,他更谨慎。他在《红楼梦辨》中说:“后半书虽有数处可观,然神气尽变。”他用的是“神气”二字。这是文学批评中极少使用的词,它不是说文采下降,而是说精神结构断裂。
两人方法完全不同:一个用资料拼图,一个用文本解剖,但他们最终走向同一个判断方向: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不具备同一创作动机。
这并不是要否定后四十回的价值,更不是为了“找真凶”。胡适和俞平伯都没有说“后四十回应当剔除”,他们只是提出一个问题:我们能否分清,“曹雪芹写了什么”,以及“后人补充了什么”?
他们没有把“怀疑”停在“风格不同”这种感性判断上,而是反复验证:“这句是谁说的?”“这句最早在哪里出现?”“这个人物的行为是否与前文相合?”
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贡献,不在结论是否确定,而在于方法——文学不是凭“感觉”研究出来的,而是可以像历史一样被逐步证实与排除。
到现在,关于“后四十回”的问题的争论其实仍未停止。但胡适开创的研究方法被延续了下来:红学家们不再拍脑袋,而是始终坚持用每一条史料、每一句原文,去构建一个能经得起反问的判断。
在我看来,这种方法本身,就是最可靠的立场。

星速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